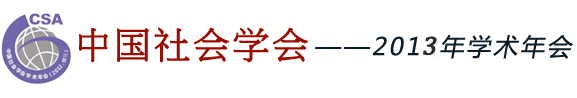为反思家庭研究的地位衰变,提升家庭研究的能力,推进家庭研究的学术自觉和学科共识,由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筹)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中国家庭研究:现状、问题及前景”分论坛,共收到论文和摘要34篇,27位学者和学生作会议报告。会议主要围绕家庭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从学科地位的逆转性转变、学科建设的阶段性梳理、学科发展的整体性调整和学科前景的定位性展望进行讨论:
一、家庭研究发展的阶段性回顾:“重问题,轻理论”。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郑丹丹副研究员统计了国内社会科学综合类最高水准期刊2012年发表的论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仅刊登了 1篇主题与家庭有关的论文,仅占全部发表论文的0.5%,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准期刊《社会学研究》共发表与家庭有关的论文4篇,占5.1%;被认为已接近学科最高水准的《社会》杂志,全年仅发表与家庭有关论文2篇,占2.5%。而《美国社会学杂志》(AJS)2012年发表家庭主题论文3篇,占6%,《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发表6篇,比例高达14.6%;况且美国还有众多家庭婚姻的专业性期刊。而中国则没有足够的发表平台,因此,学术发展空间不足,也导致研究队伍不足、后继乏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吴小英研究员认为,社会学恢复重建30年来,家庭研究曾一度有过繁荣时期,开展了大量问题导向的实证研究,这些调研成果为家庭学赢得了合法性和主流地位,然而,经历最初的安身立命阶段之后,家庭研究似乎陷入了某种发展的瓶颈阶段,一直游离在社会学的边缘地带,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无法对家庭所遭遇的现代性的种种挑战和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影响这种流变的原因虽然有多种,但从学科自身来看,主要在于其研究大多遵循着热点问题的走向和线索,而忽略了背后的主义和理论取向的探究。问题导向既为80年代家庭研究的合法化和主流化创造了条件,也为90年代中叶以后家庭研究的分化和衰退提供了依据。因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在于其独特的理论框架和解释效度。家庭研究虽然在80年代重启了私人生活的公共研究视角,为学界的去意识形态化、为社会学领域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之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但是由于理论储备明显不足,随着社会热点问题发生转移,社会学本身学科化和规范化程度的提高,家庭研究很快表现出在学术上的底气不足。因此,未来的家庭应关注更多的理论议题,在具体的研究中纳入时下流行的理论讨论,如家庭主义vs.个体主义,左派vs.右派,国家vs.市场,东方文化vs.西方文化,传统文化vs.现代文明等等。来自台湾辅仁大学的年前学生郭潇默,梳理了美国家庭学的学科建设历程,美国的家庭学有着明显的综合特征,它本身就是一个交叉学科,也就证明了家庭学的不断成长,来自对众多议题的吸纳。
二、家庭学学术地位逆变的反思:“用学显,体学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唐灿研究员,借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的“体用”辩证关系,来说明家庭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定位变化问题,进而解释了家庭学从曾经的显学变成目前的边缘学科的社会性根源。大致而言,家庭学研究在两种意义对待家庭,一种是将家庭视为直接的研究对象,所谓的“体”,即研究家庭本身,另一种是家庭是间接的研究对象,所谓的“用”,即通过家庭看社会,家庭学过去的显学时期多是“用”式研究,而家庭学当下的隐学状况多是“体”式研究,导致这种“体用有别”的研究方式转变的最终根源,是中国宗法社会-工业社会的转型:宗法社会的家国同构,决定了透视式的家庭学研究前提,导致了“用”式研究的流行;但工业社会趋势下的家庭生活分化和封闭,则决定了隔断式的家庭学研究前提,造成了“体”式研究的出现,恰恰是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变化,合力导致了家庭研究在学术共同体中的边缘化地位,也导致家庭学者们较难被其他领域的学者认可,甚至遭遇贬损或排斥,从而陷入孤立境地。不过,在工业社会及专业分工的新形势下,我们依然需要家庭,因而也就需要研究家庭,因而把家庭作为直接对象的“体”式研究,即关注微观家庭组织本身及其内部关系,应得到再次承认和客观肯定,至于未来的家庭研究出路,则应寻求更贴切合适的理论资源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而走出一条“体用”结合的新研究路子。
三、家庭学研究的整体性调整:“大视野、新领域”。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沈奕斐副教授,从国际化的视野比较了家庭研究的议题范围,欧美的家庭学研究议题不但非常广泛,而且生动有趣,如多年举办的社会学会中的家庭分论坛,会按照研究主题的不同再细分为更为小型的子论坛,与国外家庭分论坛下设多个子论坛相比较,中国的家庭研究显得视野相对较窄,议题不够宽广,很多重大议题还没进入家庭学的研究视野,如儿童性侵、家庭风险、家庭情感和家庭价值等等,为何中国的家庭学研究会如此?沈奕斐分析说国外的家庭学研究,多采用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充分考虑到家庭内部各个成员的差异,但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内没有得到重视,在很多研究中,家庭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这其中隐含着家庭成员是均质的假设,这就造成很多研究中并不重视家庭中的具体个人,因而,家庭学的研究,需要开展对家庭中不同个体的研究,需要将夫妻研究分解为夫和妻的研究,将父母研究分解为父和母的研究、将子女的研究分解为子和女的研究等。此外,还要重视家庭学研究的个体主义关怀问题,目前,社会转型带来了的婚姻家庭生活的变化,这也造成了作为个体成员对婚姻家庭变化的不适和困惑,社会上有对家庭学研究学者的理论指导的期待和需求,如不少家庭学的学者被误认为是心理咨询师,因此,家庭学的必须重视这一社会需求,家庭学的学者们不但要“走出去”开拓视野,而且还要“走到一起”加强对话,集体适时回应当下的社会需求,这不仅关涉到婚姻家庭生活的改善,而且关涉到具体个体生活的福祉。对未来家庭学的扩大研究视野和领域的探讨,也引发了家庭学的调研方法的讨论,如调查中的伦理问题,收集资料的真实性问题,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的权力关系等关键环节,都在讨论中一一展开。
四、家庭学的未来前景展望:“出后台,入前台”。南京师范大学的金一虹教授,以家庭研究为本位反观了中国的公共政策,她从公共政策架构中的家庭缺位论述出发,指出未来的家庭学应有一个转向:应从公共领域的“后台”走到“前台”。中国当前正致力于完善各项公共政策,然而,中国的公共政策中缺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政策,这点与国外包括家庭单元的公共政策差距甚巨,欧洲的家庭政策包括家庭福利政策,家庭照顾政策、家庭服务政策和家庭救助政策等内在配套的几个方面,而中国当前的家庭政策,则碎片化地集中在计划生育、儿童抚育、老年赡养和贫困家庭扶助上,对家庭的支持和服务范围极其有限,难以满足和支持多样化家庭发展的多方面需要,更为让人忧虑的是,一些政策法规如离婚法对家庭起着破坏作用,一方面,政策后果给不堪重负的家庭持续加压,如从“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到“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变化,依然属依赖家庭主义的范畴;另一方面,政策又顺应了市场的消极分化,把个体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原子化,让缺乏保障的个人去承担现代社会中的不意风险,如离婚法的自由主义导向。金一虹教授认为,面对公共政策中的家庭政策缺位事实,家庭学的研究应当有所学术担当,应当致力于在公共政策框架中构建“健康稳定的家庭政策体系”,倡导关爱家庭的政策话语则首当其冲,让家庭从公共政策平台的后面走上前台,这种政策将更好地服务于当前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社会秩序的优化。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王金玲研究员,总结了近些年家庭学的研究进步,如学术地位有所回升、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学科视野不断开拓、青年学者力量加强和与国际对话能力提升等;对未来家庭学的发展,王金玲研究员给出了可操作化的具体提议,倡导学科知识的行动化和行动的学科知识化,如以家庭专业委员会为核心,凝聚跨学科的研究力量开展研究,与其他专业委员会或相关NGO建立联系,搭建合作平台,为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深入社会创造机会和条件等,这些建议引发了集中式的讨论。
尽管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学科建设,但依然也关注了某些具体研究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晶博士,报告了子女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关系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徐浙宁副研究员,说明不同学科中家庭研究尤其是政策研究的差异问题;江南大学的吕青副教授,分析了留守家庭的调适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的副教授魏伟,分享了同性恋伴侣关系及其家庭实践;华东政法大学的马姝博士,梳理了离婚法历史变迁中的性别政治意涵变化;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魏莉莉副研究员,解释了成就动机通过养育方式实现代际传递的原因;北京科技大学的边静博士,探讨了与共和国同龄的职业女性的职业变动特征;复旦大学的秦博博士后,从性别、国家和民(种)族的多元视角来探讨中西通婚现象,这些具体研究都是对学科问题探讨之外的补充和丰富。(薛亚利)